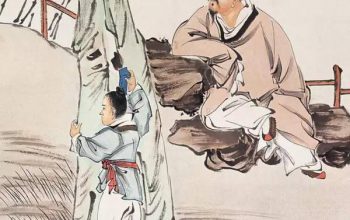文化消费,一般指人类对于精神文化产品及精神文化性服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消费活动。学术界习惯于把文化消费看作现代的社会行为,而实际上人类的文化消费行为属于一种常态的社会历史现象。只是人类在20世纪60年代完全进入“消费社会”后,文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消费,甚至连某些物质消费也转化为文化消费,即演变为身份象征与符号意义的消费,现代社会中文化消费意义才被凸显出来。
而现代文化消费意义的凸显,以至于使我们忽略了文化消费的社会历史性。追溯中国文化消费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消费的全面发展期,文化消费第一次进入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文化典籍消费、文化教育消费、礼乐文化消费等等。诸子百家对于进入自己视野的文化消费现象,形成了各自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主张。
主张奢靡消费观的管子,提倡并鼓励文化消费。《管子·奢靡》篇记载:“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欲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其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致功。”管子认为物质消费与文化娱乐消费都是民众正常的消费,因此,只有在满足物质消费的同时也满足文化消费,民众才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儒家主张“依礼消费”,强调文化消费和物质消费一样都必须与等级身份相符合,不得僭越。墨家则是以克制消费为其显著特点,主张文化消费要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与其劳动财富观相契合,形成了“节用”、“非乐”思想。诸子文化消费思想主要体现在文化典籍消费、文化教育消费和礼乐文化消费三个方面。
一、文化典籍消费
由于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不同,它是人类超出生物本能之外的文化心理需求,旨在寻求一种情感愉悦、知识交流与心灵抚慰,并希冀借助于智力开发、精神熏陶以达到文化传承,因此,文化消费以物质消费为前提,但又受到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意识的深刻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文化消费即成为与物质消费并重的日常消费。《管子》中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①,既是对物质消费决定文化消费必然性的领悟,也是对两种消费不可偏废的提醒与警策②;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历史真实的一种折射。从当时文化消费的三项基本内容看,文化典籍消费是比较普遍的消费形式。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读书与进取一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以追求知识、丰富内涵和提升能力为内在动力的读书活动,在古代文化消费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行为。春秋年间,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国日渐强盛。在周惠王、周襄王年间,因王位之争,学官四散,史官外迁,其中就有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马氏“去周适晋,”此后“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③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又发生了王子朝奔楚事件,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④,直接导致了周王室御藏典籍流散于民间。于是,以学官、史官和御藏典籍为载体的官方文化,便由中心流向周边,从官方进入民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⑤,既促成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形成了文化多中心的局面;也使官方典籍的民间阅读———即文化经典的民间消费成为可能。
文化典籍从官方垄断进入大众文化消费层面,经历了两个过程:先是由周天子的京畿流向各诸侯国,即“王道既微,诸侯力政”⑥的春秋时期;再由各诸侯国转而流入私家的战国时期。⑦先秦诸子的出现,就是私人阅读———即个人文化消费开始的标志。“孔子修《春秋》,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尝见百国春秋,其书疑皆官书之散在民间者。”“官书变为私书,则无书者固不知学,而有书者转得博学详说,??此圣哲之所以勃兴于春秋之末也。”⑧孔子为修《春秋》而多方求书、索书,《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有记载:“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另外,《尚书序正义》也有记载:“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始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墨子是先秦著名的藏书家,曾经阅遍各国《春秋》,《墨子·贵义篇》有记载:“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①连其弟子弦唐子都产生了疑问:“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墨子回答:‘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既然读书已经成为墨子生命的第一需要,那么,“载书甚多”并成为藏书家也就不足为奇。由此也可推测,墨子对于书籍的搜购与收藏,一定用力甚勤,花费颇多。墨子除了搜购书籍、收藏书籍和阅读书籍之外,他还曾经向楚惠王献书,《渚宫旧事》里有这样的记载:“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是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请过进曰百种,以待官舍人,不足须天下之贤君。’墨子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王而归。”②从这段对话看,墨子无偿献书的行为不属于经济利益驱动的市场行为,而属于超越经济利益的社会性利他行为,墨子追求的是楚惠王“用书”之后,能“行”其“道”与“听”其“义”,因此他完全不在乎献书能换来“受其赏”与“处其朝”的个人利益。这与孔子“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③的志趣,有着明显的区别。
尽管孔子在这句话的前面有“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前提、后面还缀上了“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两重道义性的说明。两位好读书并且善读书的大学者,对于文化典籍消费志趣上的差异,彰显出两千多年前中国文化消费观的多元性。笔者不妨做出这样的判断:儒家的文化典籍消费观,是在理想中追求实用;而墨家的文化典籍消费观,则是于实践中追求理想。在儒墨之外,关于名家学者惠施的图书收藏,《庄子·天下篇》有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学富五车”的典故,即由此出。惠施学识丰富的直接原因,应该是他非同寻常的文化经典阅读量与强大的经典知识的占有量。其实,阅读与占有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典籍消费的过程。从儒、墨、名三大家的文化典籍消费情况看,以墨家较为全面:从搜购到阅读,由收藏到传播,再由传播到自己的著述,墨家深入到了文化典籍消费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若从孔子、墨子、惠施等人的文化典籍消费行为看,正是他们对于文化典籍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收藏愿望与阅读冲动,他们才得以创造出一批璀璨的精神文化瑰宝。④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消费,印证了文化消费的一个最根本的规律:文化消费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过程———即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文化传承和文化再创造的过程。
二、文化教育消费
经典文化的传授与接收、掌握与弘扬的过程,是文化教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教育消费的过程。教育作为传承与发展型的智力文化消费,在西周时期还没有形成消费市场,因为西周“学在官府”,没有私学,文化教育基本上是由官方垄断。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与学术下移与士阶层崛起,中国的私学开始兴起。私学相对于西周时期的官学而言,不纳入官方教育体制,它是由私人主持、经营、管理的一种教育活动。刚开始出现的私学,没有固定的教育场所,主要以周游四方的私人讲学为主,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由一群支付了教师一定报酬并乐于接受其政治主张、教育理念和思想内容与思维方式的门生子弟为对象,在传授、接收和弘扬知识文化与道德理想的教学活动中,逐步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私人学派。因此,从文化教育消费的角度去审视,诸子百家的形成既与私学的诞生与发展同步,同时也经历了中国早期文化教育消费的完整过程。
章太炎曾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①,也就是说,由老子和孔子等学者开启端绪的私学②,打破了商周以来贵族对文化的垄断权,新兴的地主、商人和平民子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文化教育消费市场。诸子百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私学,其中作为当时显学的儒墨两家,在文化教育的消费市场中所占份额最多,影响也最大。如《吕氏春秋》所记载:“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③,而且“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④私学的规模。在儒家私学中,孔子号称先后近十代弟子,门徒数千,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⑤。而墨子私学的规模和学生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儒家。仅墨子主导的阻楚救宋活动,由其大弟子禽滑厘所带领的墨家弟子就有三百人之众,所以他可以向公输班和楚惠王非常自信地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⑥另外,《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墨家的弟子要么是“拯世救民”的凛凛义士,要么是“杀己利天下”的“任侠”,而禽滑厘等弟子,更是实施“兼爱非攻”的大师级人物,墨家动辄出动这样“百八十人”或“三百人”刚毅骁勇的“弟子军”,这也成为中国早期私学的一大特点。私学规模较大者,还有鲁国的少正卯、王骀和郑国的邓析。王充《论衡·讲瑞篇》里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能使孔子私学“三盈三虚”,竟然只剩下了一个颜渊,足见少正卯私学之盛。
《吕氏春秋·离谓篇》里记载了邓析办私学的盛况:“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作为儒家后学,孟子的私学规模更为壮观。《孟子·滕文公章句下》里,彭更问其先生:“後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於诸侯,不以泰乎?”在彭更忐忑不安的描述中,所显示出的是一支超过孔子周游列国规模的浩浩荡荡的孟子私学队伍。私学的经营管理。由于各诸侯国对私学采取不干预甚至完全放任的政策,因而私学的经营管理便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
第一,教学场地不受限制,流动性讲学非常普遍。以儒墨为例,他们基本上没有固定于鲁国一地,而是辗转于列国之间,主要活动区域在以鲁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孔子带弟子从鲁国出发,到过卫、宋、齐、郑、晋、陈、蔡、楚诸国;孟子流动讲学到过的国家最多,历史最长,游历的国家有梁、齐、卫、宋、郑、滕、鲁、魏、晋、陈、蔡、楚诸国。
第二,时间不固定,主要取决于诸位大师的个人意愿。孔子一生有三起三落的办学阶段,墨子是断断续续将私学坚持终老。
第三,教学内容不统一,各家学派讲授自己学派的思想与主张。如孔子在鲁国讲周礼,推崇礼乐制度;与孔子同时的王骀,讲老子道学;少正卯讲学的内容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据推测可知应是与孔子对立的思想。至战国,学者在私学里讲仁政,言法治,论合纵,主连横,尚兼爱,析术势,他们各立门户,自传衣钵,于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四,生源多样性。在孔门弟子中,出身寒门的有颜渊、曾参、原宪、子路;贵族出身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富家出身的如子贡;墨子的学生则多为工商业者。荀子说的“夫子之门,何其杂也”⑦,足以说明私学生源的多样性与私学的开放性。
第五,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先生。孔子的学生可以放弃儒学投奔少正卯门下;墨子早年学儒,而后弃儒而自成学派;陈相原来是楚国儒者陈良的弟子,后弃儒学农。学生自由择师的现象改变了过去官学教育中师生间的人身隶属关系,开创了新的学业师承、学统授受关系。私学的经费。私学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富人及某些诸侯国的赞助,一部分来自学生缴纳的学费。诸侯国的赞助有两种形式:一是诸侯国自愿解决师生游学期间的生活费用———即“传食於诸侯”,①如孔孟的周游列国。由于诸侯国的态度不同,传食诸侯也有遇到断档的时候,所以孔子及弟子就曾遭遇“累累若丧家之犬”的窘境;而农家的许行,弟子数十人,在滕国受到滕文公的隆重礼遇,安排食宿。
二是各诸侯国国君的自动捐款资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为博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而自动捐助。以孟子为例,齐王曾送兼金一百镒;宋国国君送金七十镒;薛国国君送金五十镒。②学生缴纳的学费以“束脩”为主要形式,同时也是拜师的贽礼。孔门子弟大多如此。③据朱熹的考证,孔子时代的束脩不太值钱,仅作为拜师的见面薄礼,礼仪性大于收益性,但它毕竟是教师的劳动所得。《朱子语类》第三十四卷《自行束脩章》里这样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真宗时,讲筵说至此,云:‘圣人教人也要钱。’”与孔门的束脩制不同,郑国邓析教人“学讼”的学费则是接受学生送给的袍子、衣服与裤子,即以送先生服装代学费。唐代学者杨倞在《荀子·正论篇》注中(他援引了《新序》注)说:“子产决狱,邓析教民难之;约大狱衣袍,小狱襦袴。民之献袍衣襦袴者,不可胜数”。④不论是孔子束脩制的干肉脯,还是邓析袍袴制的袍子与襦裤,当时私学学费基本上多采用实物学费制,这可能是中国私学初兴时期的现象,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一大特点。
中国早期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另一特点,是私学竞争有时会演化为恶性政治事件。如孔子做了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的第七天,诛少正卯,并暴尸三日。《荀子·宥坐篇》记载,少正卯被诛后,子贡问孔子诛少正卯的原因,孔子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⑤。从孔子所列少正卯的“五恶”和“聚徒成群”、“饰邪营众”、“反是独立”的三罪看,显然孔子主要是记恨少正卯曾使其私学“三盈三虚”的大不快,于是借用刚刚到手的政治权力给自己竞争对手以政治罪名,并将其置于死地。⑥郑国的邓析则是被对手假政治罪名置于死地的。他的对手指责其私作《竹刑》、教民学讼⑦,便以“教讼乱制”的罪名先拘而后诛杀⑧。如果说孔子诛少正卯事件属于私学之间恶性竞争的产物的话,那么,邓析之死———不管是被子产所杀还是被驷颛所杀,则属于私学与官学、个人与政府之争所引发的恶性事件。
其一,子产“不毁乡校”的“乡校”是西周遗留下来的官学,邓析“教民学讼”所组成的私学,属于民间法律培训学校,这种实用性与平民化兼具的私学,无疑挑战了当时的官学,同时也挑战了作为执政者子产的政治权威;
其二,邓析私作《竹刑》,而且“郑国多相县(悬挂的意思)以书者”①,直接挑战了郑国的“铸刑鼎”,即便是后来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只是说明《竹刑》胜过铸刑鼎具有强大的优势而已。从这两宗恶性政治事件来看,文化教育消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起步阶段,已经暴露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即没有保障市场平等竞争的市场体制与法制规范。滥用政治权力,将文化教育消费的正常竞争政治化,即反映出私学竞争失败者扭曲与变异的文化消费观。孔子与子产(或驷颛)恶性行为的背后,就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消费异化在作祟。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第三个特点,私学教育成就斐然,名人辈出。私学培养的学生,毕业后有三个去向:一是走仕途,“学而优则仕”,孔门弟子多走此路;二是文化传承,作为一代名师之高足,在该学派的学术领域有重大建树,从而成就一个学派,儒、道、法、名等各派多有;三是成为知识、技能、信仰的实践者,墨子的弟子多如此。以诸子百家为主导、以私学教育为载体、以自愿接受文化传承的私学子弟为对象的文化教育消费,由于接受范围的限制,使这一消费方式的普及程度相对有限,文化教育消费观念也存在着相对消极的因素。
三、礼乐文化消费
在王子朝奔楚事件中,除了带走了御藏典籍、拉走了一批旧宗族之外,还带走一大批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其中有一批乐师,这是周文化的一次最大迁移:“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汉,少师阳、击磬襄入於海。”②周王室的礼乐文化由此下移,进入民间,而礼乐文化消费也开始突破礼制的规范,逐步地社会化、平民化。礼乐文化消费,首先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的。
由于中国音乐文化从夏商周开始就与宗法社会的等级礼制捆绑在一起,因此,中国文化的肇始期有近千年的音乐文化消费一直具有礼乐文化消费的显著特点。宫廷礼乐文化消费。《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四》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齐宣王可以在宫廷中组织起300余人的专业吹竽乐队,足见当时整个诸侯国国君宫廷音乐消费的规模与水平。齐国宫廷燕乐的场面更大。《史记·孔子世家》载:“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依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围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楚国的宫廷礼乐文化消费不在齐国之下,《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日夜为乐”。宫廷的礼乐文化消费,自西周至东周,一直追求的是“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③只是随着王纲解钮、礼崩乐坏,宫廷的礼乐文化消费便逐步衰落。宫廷礼乐文化消费到春秋中后期已具全面的衰相。《论语·述而》记载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反映出孔子难得欣赏到一次宫廷高雅音乐《韶》的感受。关于孔子“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学术界多理解为具有很高音乐文化修养的孔子对于高雅音乐的陶醉与痴迷,其实孔子“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莫名惊诧,应该说明了宫廷雅乐在孔子那个时代的稀缺程度。听惯了各国民俗音乐———《风》,一旦遇到了难得一闻的《韶》———宫廷雅乐中的极品,以恢复周礼为使命的孔子自然会产生“三月不知肉味”感叹。贵族音乐消费。从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看,贵族家庭多有乐器,有编钟、石磬等乐器。这表明音乐已经走进了一般贵族家庭,成为一种普遍的娱乐活动。所谓“钟鸣鼎食”,即属于当时一般贵族家庭宴饮时的音乐消费形式。编钟、石磬等器乐,自商周以来是宗法制度之下礼制规定最严格的器乐,一般贵族不能享受这一等级的消费,否则即犯违制僭越之罪。而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的贵族或有钱人都成为“钟鸣鼎食”之家,他们打破了音乐消费等级的禁区,进入高于自己身份的礼乐消费级别。这看似突破了礼乐制度中的等级身份,而实际上淡化了礼乐消费等级的边界,使传统的礼乐消费蜕变为一般的音乐消费。民众音乐消费。《战国策·齐策第一》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这一记载既反映出齐国临淄的民间音乐和日常娱乐活动的普及情况,同时也体现出当地娱乐文化消费的实际情况。从当时的礼乐消费情况看,凡有大事皆需行礼作乐,如战争有军乐,婚庆有喜乐,丧事有哀乐等。音乐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音乐为主要内容的礼乐文化消费,开始普遍地被人们接受。至于一般的娱乐消费,在当时则更为普遍。《列子·说符篇》记载:“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可见,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中国就已经流行高跷,而这位叫“兰子”艺术家,是以高跷结合剑术进行特技表演,获得了极其丰厚的经济报酬。①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文化消费,先秦诸子以孔墨两家的文化消费观最具代表性。孔子对音乐文化包括娱乐文化,主张“以礼消费”。不过,孔子偶尔也会出现类似欣赏韶乐之后的特殊反映:齐王已经越制,而孔子非但没有谴责这种行为,反倒由赞赏到痴迷,对于一向以崇尚礼制、并以周礼捍卫者自居的孔子来说,是非常特殊的。这是否属于纯粹的音乐文化消费遭遇到传统礼乐文化消费之后的尴尬,抑或是孔子理性精神在音乐文化欣赏方面的盲区?而这也许就是孔子礼乐文化消费观的悖论性所在。
墨子的礼乐文化消费观与孔子迥然不同。
墨子的文化消费观主要体现《非乐》里,又散见于《七患》、《辞过》、《三辩》、《非儒》、《公孟》、《鲁问》诸篇。刘向的《说苑·反质》篇中也有记载。“子墨子之所以非乐也,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宇]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②可见,墨子并非简单地反对文化消费,而是将娱乐活动与“圣王之事”和“万民之利”相比较,主张以后者为重,尤其是反对以牺牲百姓的最低生活保障为代价,去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的文化消费。因此,墨家认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消费,不应该成为被统治阶级的负担。墨子提出“非乐”的第二个理由:专职艺人既脱离物质劳动实践,又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利于社会发展;第三个理由:欣赏音乐、舞蹈的文化消费活动,会影响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和劳动者的生产活动。音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因此,墨子认为娱乐文化消费是超过消费临界线之上的奢侈消费,属于异化消费。崇尚节俭,是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消费伦理原则,墨子“非乐”的礼乐文化消费观,是主流消费观的引申与发展。只不过在引申与发展的过程中,墨子由对异化消费的过度警惕而产生了矫枉过正,从而激化出“非乐”型的文化消费观。墨子的礼乐文化消费观,存在着忽视精神文化需求的局限,这在当时即引起诸子的一片质疑之声,从秦汉至明清也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异化消费产生警觉与防范的思想家,墨子以“非乐”的形式提出反对异化消费的命题,这在异化消费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陈曼娜︱天津财经大学
申明:本文来源网络,如涉版权请联系本网删除。